燃烧的艾米莉狄金森

「艾米丽 狄金森」,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外国女名。
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我还在上小学二年级,是在《读者》上看到的。彼时的《读者》还没有更名为《读者文摘》,定价不过三元一本,字淡纸薄。我从报刊亭里将薄书取出,带回家,在地板上盘腿坐下,摊开翻阅,然后在某页的角落里读到一首短诗。也许是负责杂志排版的编辑先生不小心在版面上留出了一块空地,上一篇文章长短都不能继续延伸了,于是他从稿件里挑拣出一块肥瘦适中的短诗,把它填进这块空地里;也许不是,《读者》每刊本来就固定有刊登诗歌的板块,总之是在那天我读到了艾米丽狄金森的诗。
现在回想起来,那首诗具体写了什么,题目叫什么,我都不记得了,只记得那种冷峻、细腻的情绪凝练地组合,把人带到深邃的虚空里。我盯着诗尾的句号,半晌回过神来后的第一反应是:「这是个老女人写的吧!」,遂仔细看了看作者的名字。
窗户间散落着属于千禧年初的黯淡日光,黑白印刷的铅字还带着一点墨味,少年盘着腿发愣,都历历在目。
此后六七年,我在《青年文摘》上读她,在《格言》上读她,最多仍然是在《读者》读她。我搬了两次家,结束小学升入初中,春天与秋天过去,我坐在地板上读她。我读她的《我隐藏在,你的花里》,我读她的《我生活在可能性中》,我读她笔下的花和死亡,我读她的孤独思索。
读得多了,虽然我们隔着国籍和年代不可能见面,我开始熟悉她,开始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艾米丽狄金森是个瘦瘦的但不高,苍白忧郁的女人,一双眼睛在磨损的黑白照片坚硬而发亮。我又想象艾米丽狄金森说不定是个白天把持家务、热情说笑,夜晚又会独自坐在灯下惆怅的微胖女人(反差萌也很有意思)。但无论如何,她应该度过了有趣充实的一生(或者说我隐隐如此希望着),她写的诗应该在周围乡间邻里传开、小有名气,她应该嫁了位朴实爱人但不善言语的丈夫,站在美国南部的阳光和农场的微风里。
尽管我心里知道这些画面和她诗里流露的气质不符。
初中的一天下午,我又一次盘膝坐在家里的地板上翻开一期《读者》,翻到了她的诗。这次诗的开头处居然莫名添了一则简略的生平介绍!也许是那位负责排版的编辑先生又遇到空地了,他习惯性想找点内容填充,于是搜了诗人的生平资料放上去,以期完成他的工作。
生平很短,我认真地读完了。艾米莉狄金森果真是个一生未嫁的老女人,且又是一个生前无人知晓,死后声名大噪的例子。如梵高如王小波,她的思想超出了那个时代。她生前出版的不过寥寥几部作品还被出版商大肆修改,「因为它们不符合当时传统的诗歌规则」。
艾米莉狄金森……以离群索居著称。从 25 岁开始,她就弃绝社交,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房间窗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埋头写作,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家。在有生之年,她只有少数几首诗曾被发表,剩下的上千首诗稿直到死后才被世人发掘。
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她在世的时候注意到这些作品。
狄金森不是唯一一位我喜欢的诗人,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少年年代,我的很多时间留给了读书。我一直很喜欢阿赫玛托娃,她的诗坚韧、强烈,能上网之后查资料,发现她被苏联政府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、被作家协会开除、丈夫被枪决、儿子被捕。
我曾经在 12 岁时买了一本名为《世界最美的诗歌》的诗集反复翻阅。它的开篇是《关雎》,结尾是纪伯伦,中间 P167,左边的海子卧轨于山海关,右边的戈麦自沉万泉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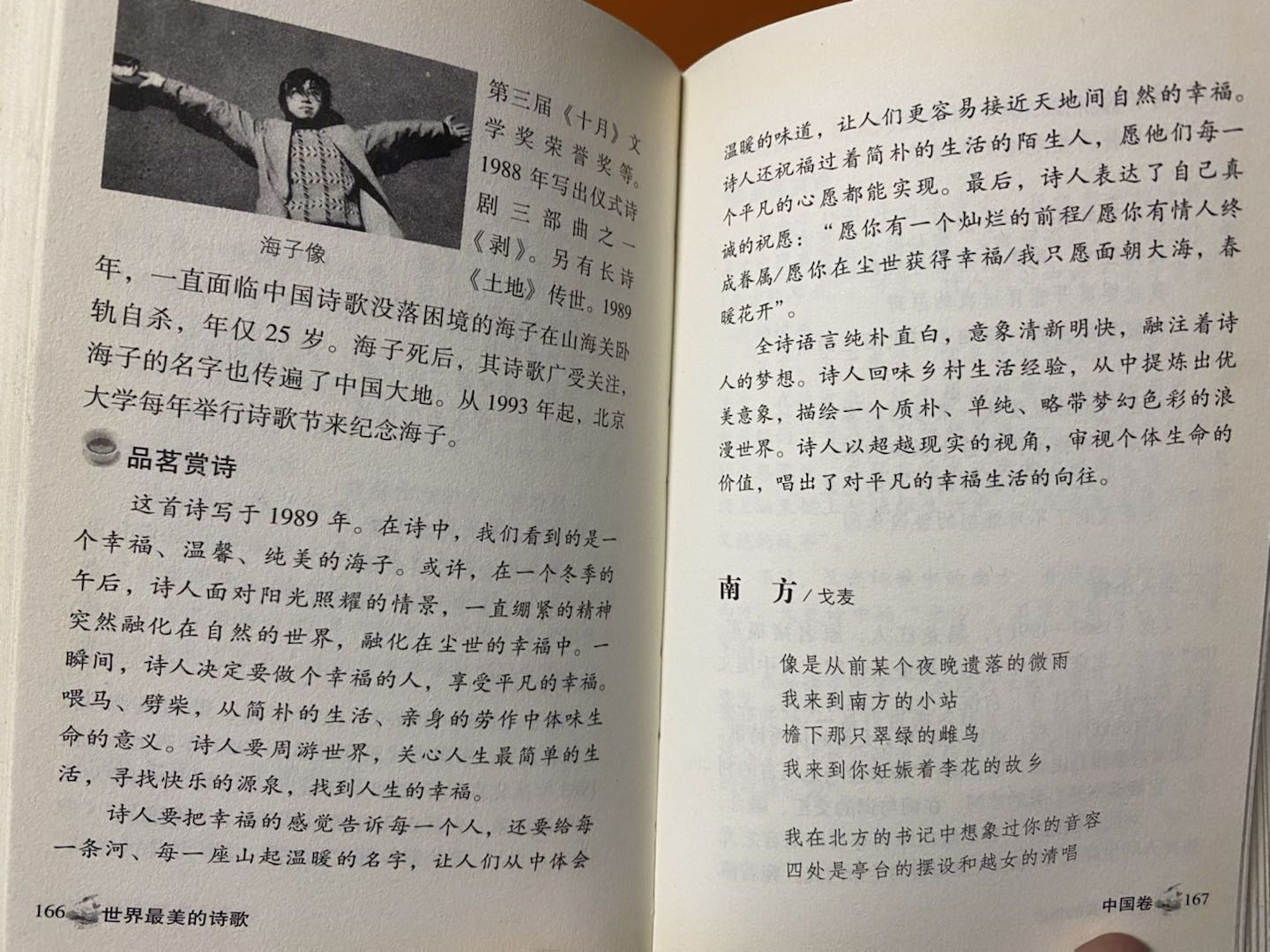
再后来慢慢地发现,写《墙上的斑点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了,写《一个女人的陌生来信》的茨威格自杀了,写《山药粥》《蜘蛛丝》的芥川龙之介自杀了。我喜欢的许多作品,它们的作者大多过着不属于「正常人」的生活,有着不属于「正常人」的结局——吞药,跳海,离群索居,郁郁不得志。
然而留下的文字振聋发聩,光芒逼得每个人都睁不开眼。
我一度产生了疑惑……难道孤寂、愤懑,经历苦难,与世界怒目相对,从不妥协直到死亡,只有这样才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吗?艾米丽狄金森,倘若她不再离群索居,过上我所想象的「农场、阳光与丈夫」的生活,就写不出我读到的那些诗,甚至我就从来不认识她这个人了吗?
再后来读了著名的「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」,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……」,突然意识到原来中国人也有这种说法。又读「国家不幸诗家幸」,读韦庄在安史之乱后写的「天街踏尽公卿骨」,读民国国难之际涌现的一批大师,读鲁迅笔下郁结如火的批判,读茨威格遗书里对世界的绝望。「好可怕……」那时候我就想,原来幸福的人都写不出伟大的作品。
伟大二字,意味着把生命作为燃料充分燃烧,燃烧殆尽了,他们就自觅安息处躺下了。
(如果你读到了这里可以回到开头,题图为艾米莉狄金森之墓,美国女诗人,1830 年 12 月 10 日-1886 年 5 月 15 日。)